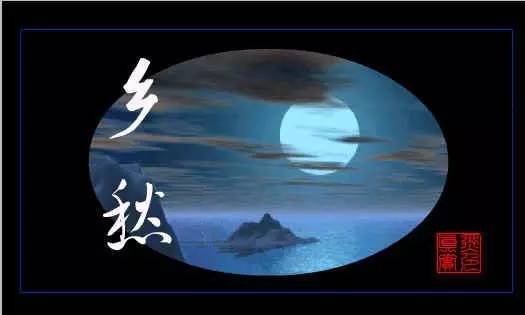
時下有一個很熱的詞叫“鄉愁”.
因為它赫然出現在黨中央的文件中。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公報明載:讓居民望得見山、看得見水、記得住鄉愁。
看來鄉愁是用來記的,這也觸發了我的心事。臺灣詩人余光中說鄉愁是郵票、是船票……,而我的鄉愁呢,竟是這一堆陳芝麻爛谷子。
一、浩蕩長江出川之后,一路東行,在漢口龍王廟與漢水交合,便折而向南,一直到九江,再轉頭向東。我的家鄉武穴就在九江上游50多公里處的長江東岸,地扼吳頭楚尾,鎮守鄂東大門,歷來是鄂、皖、贛“三省通衢”之地。
武穴原稱廣濟縣。初為永寧縣,并入過蘄春縣。唐天寶元年(公元742年)因與河南永寧縣同名,唐玄宗親自取佛語“廣施佛法,普濟眾生”之意改名廣濟縣。直到1987年10月撤縣設市才改為武穴市。為啥不改為廣濟市?后來聽家鄉領導解釋,廣濟市聽起來像廟名,不得已才以縣城名為名。

武穴秦時為鄔家閱,唐號武家閱,元代更名為武家穴,后演變為武穴。武穴港是長江十大深水港口之一,1949年 5月14日,林彪四野發起渡江作戰,在武穴至團風一線,雄師強渡,勢如破竹,蔣家王朝土崩瓦解。
這是我最早從歷史書上讀到的武穴。其實我家和武穴關系不大,他們是城里,我們是鄉下。我們那個小垸子叫“城外”,地圖上叫“城腳下”.聽著好像有“皇城跟兒”的感覺,但這個城,不是城市的城,而是城墻的城。相傳西漢開國元勛樊噲曾在此筑城,原先村后有一道兩三里長的土塹,明顯高于四周田野,北端有一個土堆,說是噲王女兒的梳妝臺。還有一種說法,是我們垸后面背靠一座蜿蜒的小山,全長一公里許,沒有山峰,山那邊有一個垸叫城里,由此猜想,這座前后一般高的矮山梁子就是“城”么?

但無論如何,這“城腳下”應該是有些淵源的。不遠處斗笠山上有座南溪寺,據說是為紀念三國時孫吳大將甘寧甘興霸而建,甘寧戰死于吳蜀夷陵之戰,長江中下游許多地方都有因他而設的廟宇。
二、我也沒有出生在“城腳下”,而是在離“城腳下”三、四里遠的湖邊小街:官橋。
父親是孤兒,兩歲沒了娘,10歲沒了爹,至今爺爺奶奶的準確歸宿地,他也不清楚。我們請好幾個風水先生也沒看明白,因為先生們意見不一致,一人一個說法,讓我們無所適從。上世紀50年代末,父親跟師傅學篾匠,師傅作主,介紹親戚的大女兒嫁給了他,他們在武山湖邊官橋結的婚。母親生我時還不滿18歲。因為她的生日是農歷11月22,而我是11月初八,換成陽歷是12月26,和老人家一天。

對于那時的官橋,我沒有一點記憶,因為三、四歲時,我就回到了父親的老家“城腳下”.后來師爺告訴我,小時候我也是個不省心的主,官橋街上有一家油條鋪,我經常領著小伙伴們去“分油條”,油條鋪老板便悄悄記上帳,黃昏再跟家里大人結帳。
我搬回來時住在三爺爺的隔壁,一間正房,一間廚房,只記得正房有一個搖籃,我成天在搖籃邊“搖弟弟”,母親接二連三的生弟弟,我就接二連三地“搖”不完。當時的“城腳下”由三部分組成,東邊劉家、畈上柯家還有本部張家。因為本部張姓相對多些,所以“城腳下”還有一個名字叫“城外張家”.聽說我們胡家還有隔壁村塘西楊家一部分原來都住在畈上, 1954年那場著名的大水災之后,畈上人才陸續搬到本部來,這里地勢明顯高些。

柯家是最后從畈上搬過來的。我記得那里有大片的蠶豆地,還記得自己坐在地溝里哇哇大哭,大概是被弄丟了,隔壁王壽垸的大人把我撿了去,又被父母找了回來。
畈上增廣叔的兒子,我們叫勝超哥,是我幼時崇拜的偶像。他是垸里最早上中學的孩子。他在豬窩里用手電筒放“電影”(其實是放幻燈片),大家都覺得神秘極了。他家后來搬到我家隔壁,成了我們多年的好鄰居。他家蓋房子的時候,他們班主任張老師還帶著許多同學們來幫助搬磚,我覺得勝超哥很有能耐,很榮耀。有幸的是這位張學先老師后來也成為我的中學班主任,還是我寫毛筆字的啟蒙老師。
勝超哥家有一位親戚和我家親戚鄰村,過年時我們常常結伴去拜年。拜年路上他喜歡講一些故事,有一次講一個長長的故事,一個英國水手長的故事,有點兒恐怖。我用心聽,聽一遍我就記下了,也給別人復述了好幾遍。
三、我是五歲半上的學。小時記憶力好,聽大人們開會,不認字就會背幾句《黨章》,第一章總綱如何如何。
那時大隊沒有小學,我開始上學是在劉家中懷叔家,垸里的幾個孩子都在那里,老師是王子壽垸的王木映老師,他常年吸旱煙,上衣右邊口袋外邊有一個明顯的圓形煙絲盒印記。中杯叔參加過襄渝鐵路建設,他家墻壁上貼著一張建設指揮部的獎狀,標準隸書寫的,我覺得很漂亮,百看不厭。

我學會的第一個字是“毛”字,估計那時全中國所有的小學生學習的第一個字都是“毛”字,因為緊接著要學的是“毛主席萬歲”.以至于到現在一寫到“毛”字,都有回到童年的感覺,不信你用鉛筆在方格里一撇一橫一橫再豎彎鉤試試,保證能讓你一下倒回幾十年。
后來我又在王壽垸上過學,在城里垸路邊“公屋”(生產隊倉庫)里也上過。三年級才搬到大隊小學,郭興邦垸后面山邊一縱一橫兩排房子。那年“6.1”兒童節前,我帶上了紅領巾。那一天陽光格外燦爛,是我的童年記憶中極少陽光燦爛的日子。

暑假,媽媽又生了妹妹,我們兄弟4個終于盼來個妹妹,這是我們家最高興的事情。并且媽媽月子里,我們也跟著有些好吃的。但樂極生悲,我在家門口的樹上掛“柴火”時掉了下來,當時摔昏過去了,糊里糊涂中還做夢,說是別人家的孩子摔下去了。父親那會兒在武穴船業社做工,隔壁喜爾哥他們用涼竹床翻過來把我抬到縣人民醫院。抬到官橋街上的時候,他們臨時歇歇,把我放在地上,汽車走過時,聲音很可怕,就像要從我身上輾過一樣。在醫院住一晚上,第二天就出院了,在家躺了一個月,姑媽、外婆都來幫忙照顧,喝了一個月“消腫散”,幸好沒留下后遺癥。
小學課文里有“劉文學勇抓狗地主偷辣椒”的故事。我也寫作文說我垸的地主婆秀爾娘偷辣椒,這事不知道怎么傳到秀兒娘的耳朵里,她來學校找我論理,我在教室的窗戶里看見她來了,心里說“壞了”,可她跟老師說找胡大寶(垸里人都叫我大寶,許多人到現在還不知道我的大名),老師說我們這里沒有胡大寶,她將信將疑地走了。

事后我很后悔,不應該這樣編排她。她家就在我家后面,兩間小茅屋里擠著一大家子人,日子很拮據。我們兩家關系很好,尤其是秀爾娘和母親很親近,父親在縣城做工,秀爾娘經常晚上來陪她說話聊天,她們睡在一張床上,她還教母親唱《梁山伯祝英臺》、《增廣賢文》等。我住在母親后房里,聽多了也會唱一點。我從小就喜歡這些,后來跟錦松哥的老婆杏花姐一起放牛,也學了一些民歌民謠,如《梁祝》里的“十送”“十繡”等。
秀爾娘有5個兒子,我跟她家老三最好。三哥小時會幾套拳腳,很機靈,因為成份不好,常年被村干部們“揪著”,所以總覺得很受屈。他喜歡勝超哥的妹妹愛珍姐,又不敢明說,經常讓我遞口信,但那個年代,漂亮的愛珍姐怎么會看上地主兒子三哥?即使她看上,家里人也不愿意。三哥很苦惱。過年大伙都很高興,他卻悶悶不樂,問他為啥?他說過一年大一歲,找媳婦更難了。

有一個夏夜,他睡在我家堂屋的大鋪上,約好半夜去偷瓜。想著生產隊栽瓜看瓜的是我三爺,抓住了也無所謂。到瓜地里,分不清生熟,見了白的就摘,摘到我背不動了,我小聲喊: “三哥走吧,差不多了”.回來的路上,三哥責怪我很不成熟,哪有做賊當場喊人的?第二天,小姑陪三爺上街看病,要我幫著推車,三爺一上車就發現問題:“車上怎么有這么多生瓜”?原來昨晚偷回來的瓜都放在架子車里,還沒來得及換地方。
后來三哥一家搬回楊家小垸了,地主帽子也摘了,三哥娶了漂亮媳婦,生了兒子。現在在深圳跑運輸,有時過年回來見見面,偶爾打打電話,但一接上腔就說不完,說說笑笑真的很開心。
四、小時候最期待的事情是“上街”,武穴街就是我們心中的“天堂”,大人說明天上街,這一夜準睡不著,巴不得天亮。
街上解放食堂兩角錢一碗的海帶湯讓人喝了當時血往上涌,頭暈暈的,晚上回來立馬不起夜,一覺到天亮。還有國營食堂一角錢一碗的清湯(餛飩),向陽食堂三角錢一份的粉絲肉片湯加幾片西紅柿,讓人現在想起來還饞饞的,滿嘴生津。

雖然父親就在街上,但很少有上街看父親的機會。母親給我上街的理由大多是跟垸上人一塊上街賣東西。跟銀姣姐還有垸里的大姑娘們一起上街賣辣椒,挑十幾斤辣椒走15里,到縣城天才亮。后來姑媽知道了批評母親要不得,不怕把孩子腿走壞了。但我卻很興奮,第一筆買賣做成了,7分錢賣了一斤辣椒,就趕緊到對面買斤西紅柿吃。第一次生吃整個的西紅柿,真美。賣完辣椒后,到劉家巷船業社找父親,父親聽說我來賣辣椒,還買了西紅柿,開心的笑了,留我在他宿舍住一晚。父親睡的是鐵板床,父子倆擠在一張單人床上,我一動鐵板就響,我生怕父親吵我,一夜不敢動。

還有一次上街賣蠶豆。母親頭天晚上把泡好的蠶豆裝在籃子里,教我五分錢一茶缸。我裝一茶缸總要在籃框上磕一下,這樣就不滿,還得再添點才夠,母親說千萬記住別磕了。但第二天,我還是忍不住要磕一下,所以我賣得最快,垸里一起去的人還剩很多的時候,我就賣完了。
賣得最多的是父親的作品:斗笠。和父親的徒弟一起到鄰近各村賣斗笠是常有的事。說是賣,其實是賒,誰家拿走了斗笠,記上帳,年底再逐一去討錢。

本來是理直氣壯地去要帳,怎么就變成“討”了呢?時間長了就知道,這個“討”字把家鄉手藝人的辛酸概括全了。天寒地凍的,為幾塊錢,去人家家磨半天,不是討是啥?有的跑好幾次人家還不給。特別是下大雪,別人家的孩子躲在家里烤火,而我還要跟著徒弟們去“討錢”,腰里別把“刺刀”(父親的徒弟用竹片削的),邊走邊扯著嗓子喊“穿林海,跨雪原……”,顯得很豪邁,實際是沒辦法,討不回來錢,父親臉色就不好看,因為年前要不來,開春就更難要了。
五、父親的手藝讓我家的日子算是過得去。
那年月大伙都窮,我們垸一個工(男人干一天的工分,算十分。婦女干一天七分,小孩只有四分)只值一毛多錢,到年底生產隊分紅的時候,家里孩子多的,大部分都超支,即一年干活掙的工分折算成錢還不夠買口糧,差多少就超支多少。

我們家每年都超支,每年年關生產隊分紅的夜晚,父親總是用手絹包一包錢交給會計,別的進錢人家還等著這些錢過年呢。
年底能進錢的只有少部分勞力多孩子少的人家,大部分家庭都是超支掛帳,平常則是靠賣雞蛋換點零用錢。自留地本來就不多,能賣點菜也是從自己碗里省出來的。
但孩子們有孩子的辦法,他們大都會捉黃鱔。我也賣過黃鱔,但那都是弟弟們的勞動成果。我生來不會弄黃鱔弄魚。有次放學回來,見田里一條黃鱔躺在那里,便抓回來,二弟看都沒看,說那黃鱔肯定是病了,三弟一看,果然病得不輕。
我喜歡和伙伴們在河道里“竭澤而漁”,攔起一段河道,打一道臨時壩,用臉盆、水桶拼命往外舀水,把攔住的那一段水舀干了,魚、蝦、黃鱔之類就自然悉數入簍。再往上面打一道壩,往下邊“解水”,可以省一半力氣。我的工作大多是看住壩,別垮了,相當于“望風”之類的活兒。
這時候我就特別佩服小舅。小舅智商有些欠缺,在同一間教室里讀了6年書,終究沒升上二年級。但小舅在撈魚摸蝦方面靈動得很。外婆家養了一群鴨子,全靠小舅逮青蛙喂大。我跟在小舅后面,他大老遠就能聽出青蛙的位置,并且準確判斷青蛙逃命的方向,然后一個箭步撲上去,十撲九中,很少脫手。后來小舅跟人學打井,也非常精到,他從不計算,但井口挖得特別圓,井筒修得特別直,還一個人坐在深井里悠閑地吸煙。是我不讓他打了,一是害怕會出事,二是他不會算帳,問他打一米井多少錢?他說25,打10米多少錢?他說230,越深錢越少,這井確實不能打了。

本世紀初,我把小舅介紹到鄭州一位老鄉的飼料公司打工,一打就是十幾年,每年有三兩萬元收入且吃喝不愁。每到年節,我們兄弟都鄭重其事地帶著禮品到公司看他。但這幾年小舅不太想干了,逼問之下,他說出了一個社會學家的永恒命題:我不知道這樣干下去有什么意思?
小舅真把我問住了。我知道他想說什么,快50的人了,沒老婆,也沒孩子,為誰干?這確實是一個問題,也是我此生的一大憾事。盡管為了給小舅張羅媳婦,我不止一次請人說合,光茶飯都不知賠了多少回,每一次小舅都很期待,每一次結局都一樣:竹籃打水一場空。
莫非真讓父親說中了,小舅就是單身命?

今年我力主為小舅在村前塘邊蓋了一處新房子,原來的房子長時間無人打理,破舊不堪,堂屋里長樹竟然把瓦都撐壞了。姨父很用心,把新房子弄得像模像樣的,我回去又和母親、姨父一起上街幫小舅買家具、電器,應有盡有,一切全新。幾天后小舅打電話跟我商量家具的事情,我告訴他一切都安排好了,不用操心,小舅很爽。但愿小舅今年過年過得開心些,但愿小舅此生有一個好歸宿。
六、小時候日子苦,經常沒油吃。生產隊每年菜籽下來的時候,每人一斤油,半年都不夠,所以還有半年便是沒油的日子。
上中學的時候帶菜到學校,沒油的四季豆母親盛一大碗,多是多,但一點味都沒有。有一次放學回來,母親炒包菜,覺得特別好吃,母親說是父親把生產隊挑油的桶帶回來了。
那時候最喜歡垸里誰家生孩子,全垸人都去吃面條,新鮮的肉湯澆進剛出鍋的面條,好吃極了。再就是盼著生產隊死牛,全垸人也可以飽吃一頓。

農忙時生產隊集中做飯,各家送米去,自己加好水。開飯時大多都是滿盆的稀飯,盆里照見碗,碗里照見人,一蕩一蕩的,端都不好端,把負責煮飯的大姑累得滿頭大汗。偶爾誰家蒸一盆干飯,大家都眼饞極了。冬天參加水利建設(家里人叫“挑壩”),挑一晚上,隊里分一盤干飯,再加一碗冬瓜湯,感覺很享受。但許多人把湯喝了,米飯卻舍不得吃,留著帶回家給老婆孩子們。
天干或青黃不接的時候,經常沒菜吃。母親就煮海帶,我們都在海帶里找肉,母親說哪來肉啊。沒肉的海帶真難吃。
遇到陰雨連綿的季節還動不動沒柴燒。山上的杉樹枝沒等黃就被人整下來,剛挖的樹蔸也往灶里塞,恨不得把頭伸進灶窟窿里吹也燒不著。有一次我干脆“罷工”,不做飯了,上床睡覺!睡到半夜,二弟搖醒我,叫吃飯,直到現在我都不明白二弟是怎么把那頓飯弄熟的。

所幸那時父親不在家,省下他的口糧貼補全家,加上母親會打算,所以家里從未斷過糧。但許多人家都遭受過少糧的磨難。有一次上學的路上碰到外婆,外婆掂一籃蘿卜,送給她的娘家。她遞給我一個蘿卜,站著不走。我問她還有么事,她說要看著我剝蘿卜。我剝下蘿卜,外婆把蘿卜皮裝進籃子里走了。望著外婆的背影,我的眼睛都濕了。
中學離外婆家很近,有時候母親讓我傳話或送點東西給外婆,外婆總是先下碗面條給我吃,然后她們就著面條湯煮剩飯,我們叫“湯飯”.有一年外婆病了,媽媽讓我上街買瓶罐頭給外婆,不知怎么罐頭被摔到石頭上,毛巾蔸里只剩橘子,甜水全沒了。我只好硬著頭皮給外婆送過去,外婆沒有怪我。后來母親知道了,好一頓責罵,外婆很心疼。
七、苦歸苦,活還得干。
我喜歡一個人整菜地。先挖一遍,再梳一遍,把大坷垃梳到溝里,拍細,再弄到地垅上,老家人叫菜園方。我弄好的菜園方平平的、細細的,像藝術品,弄好后自己很有成就感,經常得到母親的夸獎。
母親是屬雞的,父親常說屬雞的“賴得攤”,就是干活特有耐性。有一次我和母親一起在菜園里澆水,一直澆到月亮下山。冬天她帶我到田里“撿谷”(生產隊收完稻子后有一些遺漏),撿到太陽偏西還不回家吃中飯,我也問出了小舅的“命題”,我們為什么要“撿谷”?母親說為了冬天能吃飽肚子,我說現在我都餓得呱呱叫怎么辦?母親無語,那回家吧。

那時候最羨慕有奶奶的人家,可以按時吃飯。母親常年在田里、地里,忙完公家的再忙自己的菜園,一年四季都在忙,家里做飯倒是可有可無的事情。所以,放學回來書包一放趕緊做飯,就成了我的“作業”.開始沒有灶臺高,提鐵鍋經常要搬櫈子墊腳才行。有一次煮好飯后,把飯放到地上,沒注意讓豬吃了,母親回來好一頓責罵。
家里兄弟姊妹多,父母壓力大,干活挨罵是常事。有一天凌晨,父親讓我們跟他一起去打場,我和二弟牽牛繞場轉,好睡覺的二弟本來就沒睡醒,轉著轉著又快睡著了,牛拉屎拉到稻子上,惹得父親勃然大怒。

大人留給我們的除了害怕,還是害怕。上初中時有一次在機車下供銷社前,垸里的小伙伴搖手扶拖拉機,我幫著拉三角帶,不小心把左手夾到三角袋里,結果無名指弄斷一節。我把“斷指”撿起來用紙包住裝進書包里,也不敢給家里大人說。上學的時候用帶子把手吊上,這樣不痛,放學回來又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。半個月后,書包里的“斷指”完全干了,母親才知道我手指殘缺,問我是怎么回事,我支支吾吾地也不敢明說。
那時最高興的是去姑媽家。姑媽家在武山湖邊的廖祥垸,比我們“城腳下”大多了,分前山,后山。雖然離我們家很遠,要走大半晌才能到,但上姑媽家是父母最大的恩典。姑爹姑媽沒孩子,特別疼愛我們,我童年的幸福時光幾乎都是在姑媽家度過的。可以不干活兒,可以自由自在地看書,更重要的是沒有人責罵。
姑媽特別會做吃的,快臭的魚也做得很香。村里干部派飯常派到她家。姑媽家有一張小方桌,被擦得紅紅的,溜光發亮。夏天,別人從田里干活回來的時候,姑爹把小方桌端到門口,端上幾樣飯菜,和那些一身泥一身汗、扛著家什從身邊走過的勞力相比,這家老小的日子很悠閑,很愜意。
吃完飯就上山搭鋪,那會兒大家夏天都在山上乘涼。說是山,其實是村頭一個地勢高的平土坡,靠近湖邊。山上有兩棵大松樹,涼風吹過,松濤陣陣。白天許多五顏六色的蜻蜓在山上飛來飛去,像是蜻蜓在“趕集”.黃昏時分,垸里大人、小孩都往山上搬櫈子、門板、被褥、枕頭,鋪上就睡。上點年紀的婦女大多光著上身,山上便成了“乳房展示會”,看來看去,還是姑媽的最好看,那是我心中最初最美的凸弧。

姑媽還有一個侄孫子叫廖肅清,大家都喊他清爾哥。那是我崇拜的第二個偶像。開始他是大隊小學的民辦老師,他懂得真多,三國、水滸、紅樓夢,自從盤古開天地,三皇五帝到如今,沒有他不懂的。只要他在的場合,都很熱鬧,大家肯定瞪著眼睛聽他講。
我考上武穴中學的時候,清爾哥考上了廣濟師范,那是我們縣的最高學府,很多農村孩子都很向往。姑媽來看我們倆,在他學校住了兩晚上,又到我的學校住一晚上。考大學那年,清爾哥問我準備考什么大學,我不加思索說考武大吧,想著他會笑我說大話,可他卻堅定地說:“相信我寶能考上!”讓我倍感溫暖。
清爾哥后來當了家鄉兩個中學的領導,兒子女兒也很有出息,兒子在鄭州工作,清爾哥也經常來河南,到老了還是很健談,有很多事情,比如說紅樓夢里李紈為什么叫李宮裁,我還得請教他。
八、每個人童年都有夢想。
我的夢想非常可笑,想著自己要是周總理的孩子就好了,我就在垸西邊的大樹下蓋一幢兩層小樓,里面就住著我自己,樓里有一張乒乓球臺,我想不讓誰打就不讓誰打,想吃什么就有什么,最好是天天有雞蛋皮煮粉絲吃……因為在學校里打乒乓球老被人欺負。學校乒乓臺少,學生多,打乒乓球有一個破規矩叫“考資格”,排隊排半天輪上你打一回,打一個球考不上資格,就讓你下了,又去排隊,心里特別不服氣。本來練的機會少,打不好,再加上心里緊張,自然就是上去就下來,還老被人恥笑。雞蛋皮煮粉絲是我心里最好吃的飯,因為姑媽做這個最好吃。
有一次上學路上,見隔壁垸兩個年輕人在路上騎自行車,他們翻身上車的身姿瀟灑極了,一會兒襯衣就被風吹得鼓鼓的,我想我將來也得讓風把襯衣吹得鼓鼓的。
那年冬天,有一位同學在公路上被汽車軋死了。接連幾天,都有警察找到我,詢問當時的情況。他們在路面上量來量去,嘴里還說著“正常行駛路線”等專業術語。那會兒我就想,交警很神氣,所以考大學報志愿時我不假思索就報了法律系。
初中畢業時縣城人突發奇想,武穴中學第一次從全縣農村招100名學生,我們官橋中學只有我和陳友弟等4名同學考上。剛上武中時,有些不適應,一是縣城孩子老說我們是鄉下人,自尊心受到傷害;二是小學到初中的許多同學都到大金高中讀書,我的發小波伢、治伢也在大金高中,自己在這里很孤獨。所以母親來看我時,我哭著要轉到大金高中去,母親勸了好半天才讓我穩住。
慢慢地感覺倒好些了,因為考試多了,我揚眉吐氣的時候也多了,每次考試我都是全校文科班第一名,讓那些城里的同學刮目相看。在同學中我也有些發言權了,我要求他們不能再說鄉下人,實在不行說農村人也能接受,現在想來真有些豈有此理。

由于記憶力特好,別的同學歷史地理書上劃上一道一道的,特別是那些復讀生更是劃得連自己都看不清楚哪是重點,而我的歷史地理書幾乎都是新的,該背的不該背的我都背下來,甚至注解也用心地記,考試前我只要溫習一遍就行。數學我也很認真,高一時教數學的陳老師板書相當嚴謹,黑板一幅一幅地用,從不在黑板空白處亂涂,等號用尺子畫。我學會了,任何時候數學卷子都清清爽爽,等號兩橫直直的像尺子畫的一樣。
高考那年,分數線是383分,而我考了433分,全縣第一名,高出第二名26分。老師讓報清華、北大,我說太遠,路費太貴,還是報武大穩當些。有同學說你語文好,學中文吧,我說一輩子靠寫文章賣飯吃太累,還是報了法律。
大學四年級到長沙法院實習時,才發現自己不是當法官的料,心太軟,誰說的都有理,判誰輸都不合適。并且法官也很累,一個案子接一個案子,永無消停的時候。所以畢業時還是到了報社,還是靠寫文章混飯吃,一輩子跟“本報訊”掰扯不清。

現在應該說除了當交警,所有的理想都實現了。在鄭州住的是兩層樓,在信陽自己一個人也是兩層樓,信陽體育局還送來了乒乓球臺,鄭州杜哥又送來了自動發球機,自己經常對著機器打,水平也有所提高,現在要“考資格”估計問題不大。只是不能想不讓誰打就不讓誰打,除了司機,想讓誰打誰還不跟你打呢。雞蛋皮煮粉絲自己也經常做,但無論怎么都做不出姑媽的味道。
小時候母親說,街上的樓房有一間是我寶的就好了。為這,我在武穴街上買了一套房,十樓電梯房,緊挨江堤,站在窗前,江面上船來船往一覽無余。裝修好后,母親不愿去住,給他們一套鑰匙,他們也只是偶爾去打掃一下房間。
九、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幸運。
父母沒有給我充裕的經濟支撐、顯赫的家族背景,能把我們拉扯長大并盡可能地多讀些書,已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。但他們給了我極好的天賦,上學時學過的古文全會背,毛主席詩詞幾乎都會,以至到50歲了,還能強記《大悲咒》、《弟子規》、《滕王閣序》。
然而,除了背書,父母給的發揮得不夠。寫字不努力,拉二胡也不努力,或許是記者淺嘗輒止的劣根性使然,干什么都不精,如果能在一個方面有刻苦精進的精神,也許會有所成就,也不至于什么都是“半瓢水”.所幸在主體業務上還不太懶,“本報訊”不敢懈怠,否則連吃飯的本錢都沒了。

但命運之神對我似乎特別眷顧,一路走來總遇到好人幫我。工作很順,無論是在鄭州,還是在北京、濮陽、信陽,都能得到領導賞識,都有幾個鐵桿兄弟死心塌地幫我。
在老家武穴,有一位兄弟人稱老八。老八脾氣暴躁,卻有一個反差極大的名字:余良。1998年他來鄭州找我,我們一見如故。這么多年,從來沒在我面前說一個“不”字。八弟重孝,把我的父母看作自己的父母,連他的妻子兒女都把我家的老人當作自家的老人。有一年父親病了,被鄉親鄰居送到醫院,八弟聞訊趕到后,反客為主,千恩萬謝,鄉親們都很感動。后來父母親幾次住院,都是八弟一手張羅,等我回去,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八弟常對我說,大哥在外千萬莫羨慕人家的錢財,老了回來,你兄弟有的是,我不想到那地方去看你。

我自己的三個弟弟一個妹妹都很爭氣,這也是我的福份。我和老三的性格像父親,而老二、老四、妹妹更像母親。
我也認識一些“老大”,他們都和我一樣,盡心盡力,但大多沒有我這樣的成就感,為啥?我的樹一栽就活,而且很快成林,而他們的樹成活率不高。好多次家里吃年飯,他們都舉杯感謝我,而我真從內心感謝他們,是他們讓我有成就感,也讓我找到“老大”的感覺。
作者 | 胡巨成
整編 | 武穴新媒體中心







請輸入驗證碼